鄭朝暉論語說文:驕傲的倔強——再讀《蘭亭集序》
原標題:鄭朝暉論語說文:驕傲的倔強——再讀《蘭亭集序》

王羲之的字,在不少人眼裡,還是流麗溫婉的,但是,昔梁武帝評論王羲之的字卻是「龍跳天門,虎卧鳳闕」。這一年幾乎每日臨習《懷仁集聖教序》還有孫過庭的《書譜》,雖說一個是集字,一個更是在理解王字基礎上的創作,但都是公認的王字法流,臨習日深,越能夠感受到王字背後的雄強之氣,真的當得起「龍跳天門,虎卧鳳闕」這八個字。
由字及文,不妨再來談一談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以前寫過一篇《迷之感傷話蘭亭》)。如果順著他書法中「雄強」的角度再去看這篇文字,或許就會有更多新的看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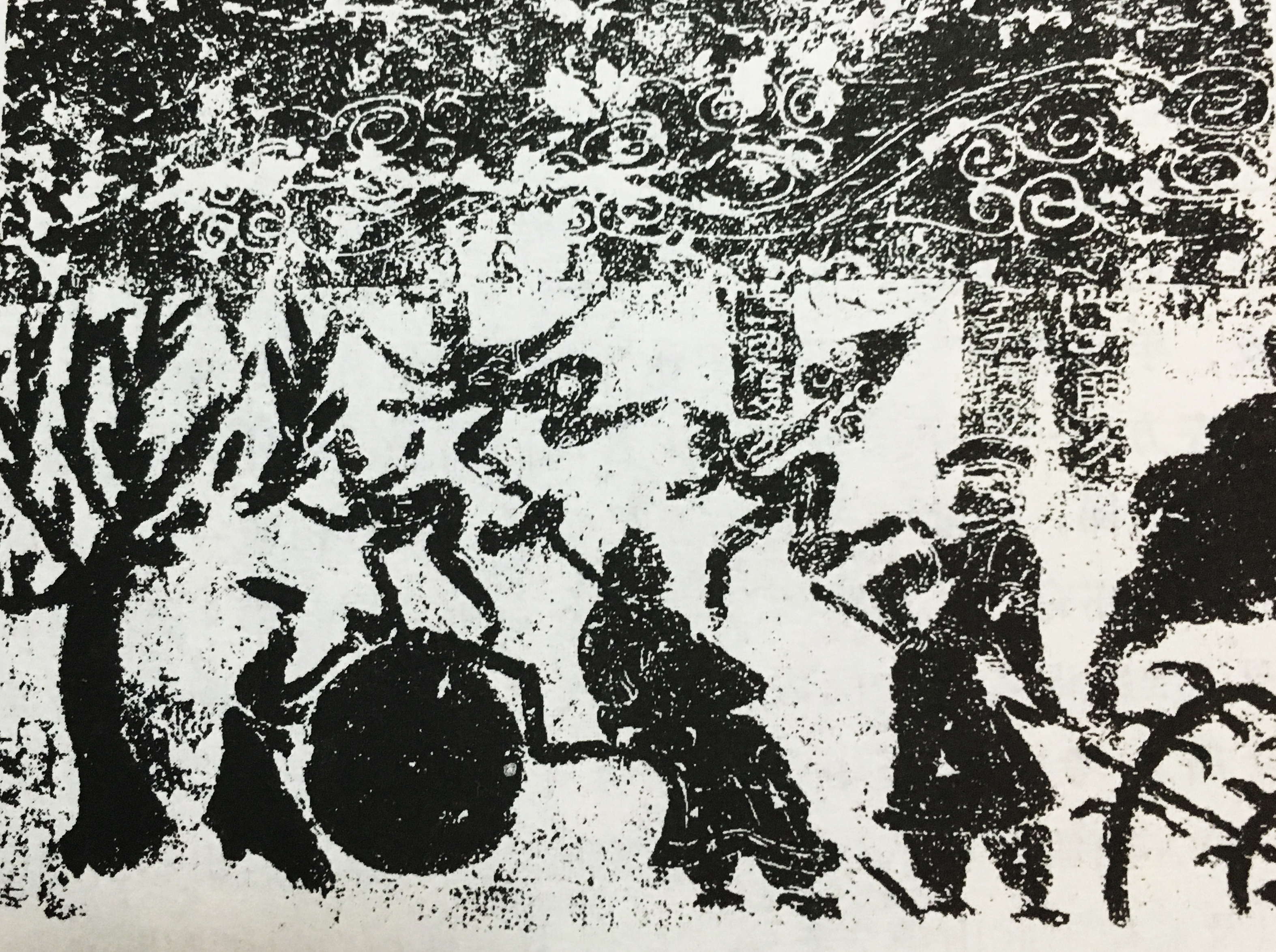
《蘭亭集序》主要的情感線索是「樂」—「痛」—「悲」。
在敘述了時序、事由、人物和環境之後,作者由衷地發出了「信可樂也」的感慨。而在感慨了人生苦短之後,王羲之有了「豈不痛哉」的感慨。而當發現這樣的生命之痛
,不僅存在於當下,而且是亘古不變的宿命的時候,他直接發出了「悲夫」的慨嘆。然而,這樣的悲傷里,卻有著極為深刻的反抗性,這是《蘭亭集序》最為可貴的地方。
「暮春之初」,雖然只是對於時序的敘述,但是這恰恰是作者所有情緒的觸發點。暮春時節,是詩人最容易感懷傷時的時節。落花飄零是很容易引發多情者的悲哀的,這很容易理解,但是暮春之初,則這樣落花飄零之相尚未呈現,但是敏感者已經能夠預感這樣的景象的發生了。這種將來未來的時節,其實是最有張力也最具審美的意義的。而王羲之身處的環境,則是崇山峻岭之、茂林修竹,清流急湍映帶左右,這是自然景物之美;身邊則是群賢畢至、少長咸集,這是人物之美,而此時正值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之時,則是氣候之美。古人所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一時俱在,自然是「信可樂也」。這個「信」字,是一種由衷地讚歎,但同時仔細品味,你也可以發現,「信」字的多義性,直接造成了一種微妙的轉折的效果。這個「信」字,既收煞上文,實際上也就引出了下文的感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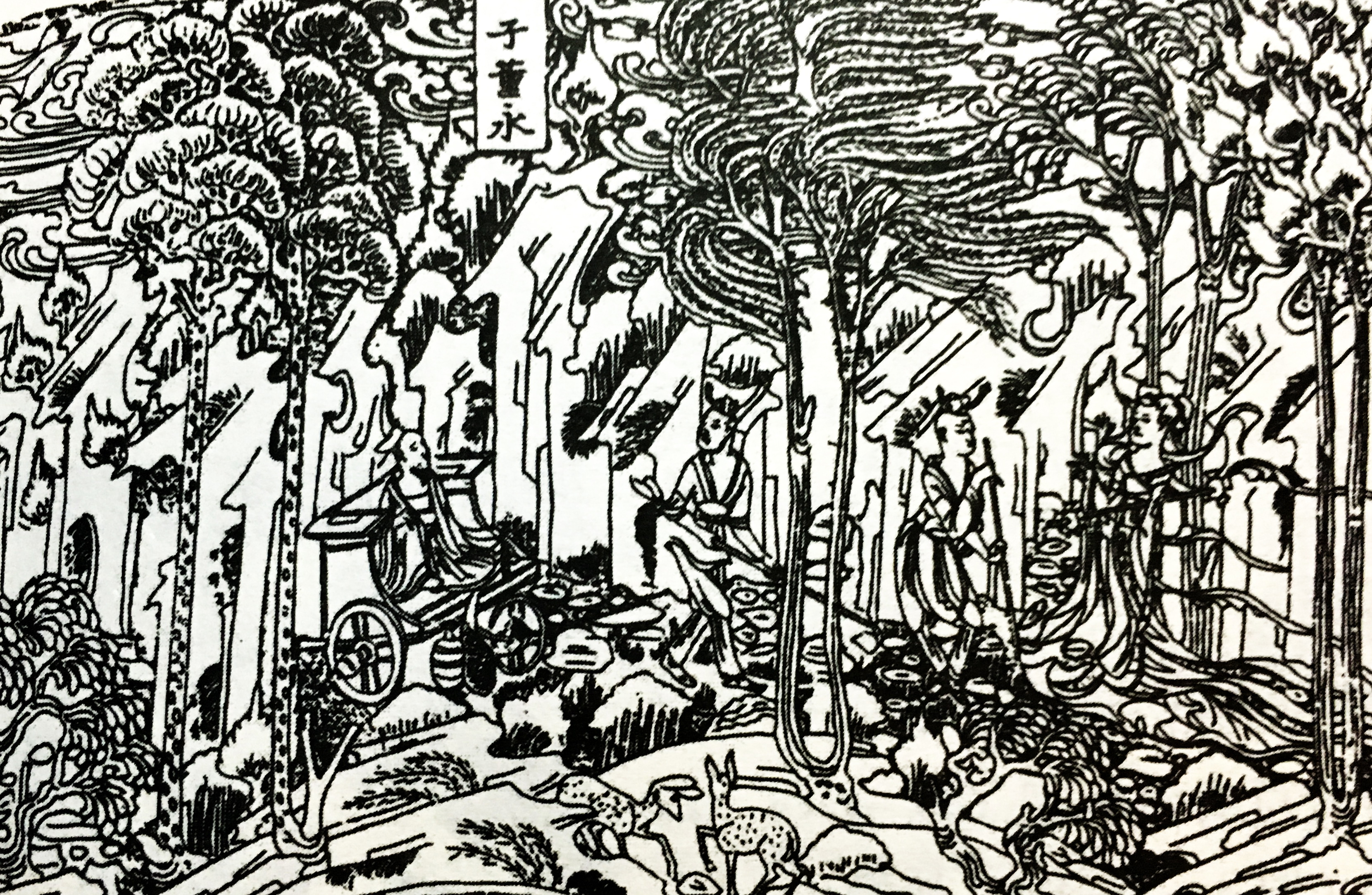
由美景美情轉而思考世事人情,作者的心緒不僅黯淡下來。身邊固然有知己好友,自己在自然之中自然也可以放浪形骸,但是這樣的稱心快意,其實都是短暫的。不過王羲之在這裡有一句說得未必好,那就是「以為暫得於己」。其實,對於那些沉浸在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中的人來說,並不會十分清醒地意識到一切都是「暫」的,痴人總是在夢中,總以為此刻即永恆,只有清醒地意識到生命短暫的人才能夠分明地知道,這種愉悅美好其實是轉瞬即逝的。所以,如果從夢中痴人的看法,這句話應該說成「以為常得於己」才對。但當一切讓人心生厭倦的時候,人們的心情也會隨之而沮喪失落。
這是從人尋常的心理感受方面說的;更何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這是講生命的終將消逝,是從客觀的生命規律上說的,當然,這句話中還隱含著對於客觀規律不可捉摸的感嘆。這樣一想,自然會發現,越美好,越難過,越珍惜,越痛苦。「豈不痛哉」,是當然的感受了。其實,王羲之最初在這裡寫的是「豈不哀哉」,但是在原稿中,他用更粗重的筆畫,將「哀」字改成了「痛」字。我分析原因有二,一是因為「痛」,更能夠表現那種直接的瞬時產生的痛苦,而「哀」不免顯得柔弱綿長了,並不符合當時那種猛然獲得的心理感受。另一方面,從語音上說,「痛」更響亮,更有力,在這裡,就彷彿一個突然出現的驚嘆號一般,讓人心驚。

如果仔細推敲我們不難發現,這樣的生命感喟,恰恰是產生於前一段「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一句的,那個能夠引發快樂的緣由,恰恰又是悲痛產生的原因。這真是一個「兩面神」啊!以此時之心觀此刻之景,自然是「可樂」的,但是以未來之心看此刻之景,則又是「悲痛」的。此刻的景並沒有變化,變化的則是我們對於生命的態度與理解。
當然,這種痛苦的感慨,不過是當年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具體化而已。我常常對小朋友們說,孔子是漢民族的文化英雄,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有時候真的只是用隻言片語就規划了整個民族的思想的範式與精神走向。所以,如果王羲之只是寫到這裡就戛然而止,也不過是將一個文化母題具體化、情景化而已,固然很美,但是卻沒有出現更深刻的主題,文章自然會顯得相對平庸一些。
然而,王羲之這樣才情飛揚的人,自然是不會就此停止自己思想的腳步的,他接著說: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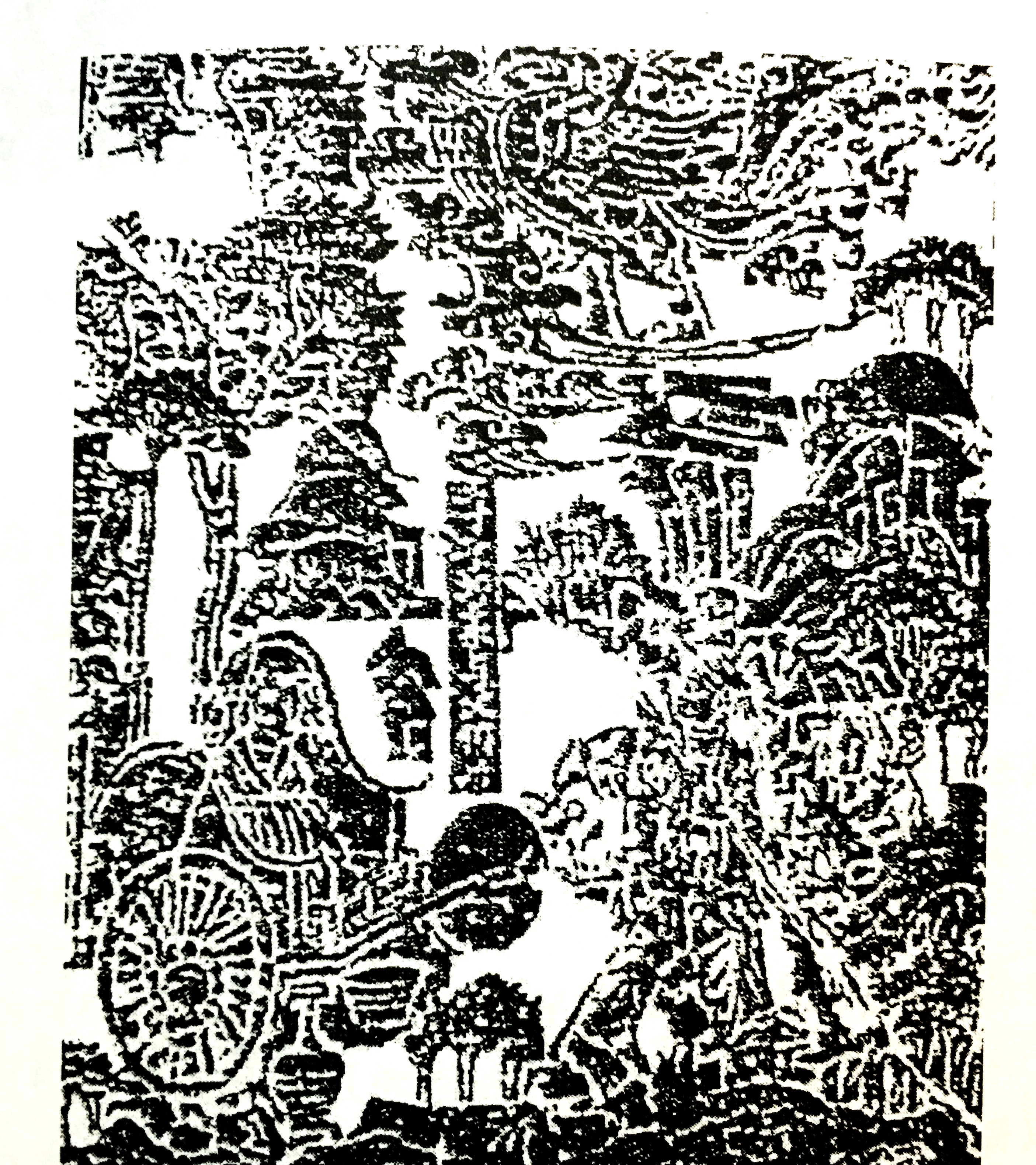
在這裡,王羲之不能明白的不是瞬間與永恆的矛盾,而是這樣的矛盾早就被人們發現,卻一次又一次在這裡生髮感慨。「不能喻之於懷」的,不是自然美好生命短暫的矛盾,而是人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揭示這樣的矛盾,「若合一契」。在這樣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感慨中,王羲之發現談玄說法,以「一死生」、「齊彭殤」來矇騙自己,其實是做不到的,而且這樣的感慨,不僅今天會產生,將來還會不斷地產生,想想人類的這種宿命,自然悲從中來,一個「悲夫」裡面,有多少感慨在其中啊!這裡原稿是「也」字,後改為「夫」,從語氣詞的角度去推敲,會發現古人對於語氣詞的表情達意功能有多麼關注。
而我真的覺得感慨良多的是那個「故」字。想一想,昔人興感,今人嗟悼,今人嗟悼,後人興嘆,似乎是一個無窮無盡的輪迴,但是即便如此,王羲之依然要「列敘時人,錄其所述」——因為,記錄本身就是對於這樣的人類宿命的反抗。這很像西緒弗斯的苦役,當推石上山被看作一種不可逭逃的命運,這隻能說明人類的放棄與屈服,但是當他把推石上山看作自己主動的選擇的時候,則體現出了對命運的反抗,更何況,文人一遍又一遍地揭示這種生命短暫與自然無窮之間的矛盾,其實就是在時間奔騰的波濤上一遍又一遍地書寫「不甘心」,從不曾放棄。這就是一種對於命運的反抗了,人類也就因為這樣的反抗而了獲得了自身的意義。甚至可以說,人類的全部意義就在於這種反抗。
我們說王羲之的「雄強」,其實就表現在這裡。明明知道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但是依然這樣去做,而且也希望這樣的努力世世代代延續下去。——有時候想想,也真的為執拗倔強的人類自己感到驕傲。於是想到了五月天的歌詞「我和我最後的倔強握緊雙手絕對不放」。


TAG:樂藝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