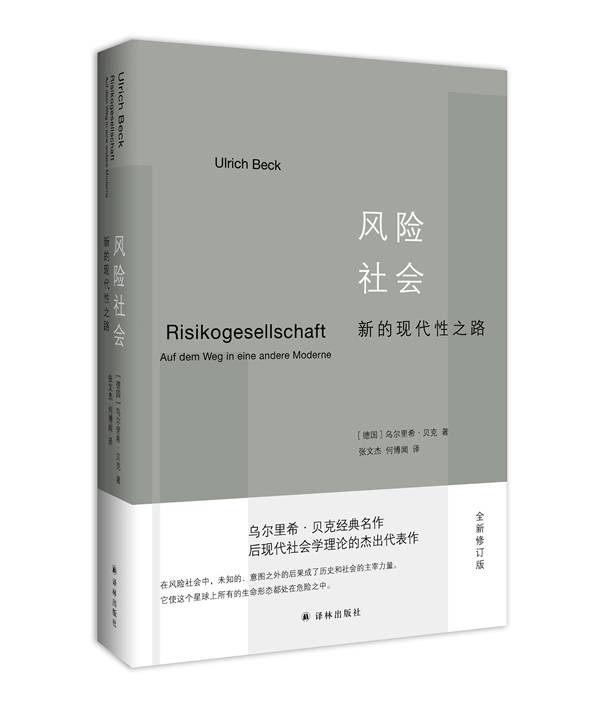什麼是風險社會?普通人此起彼伏的風險富人也逃不掉
原標題:什麼是風險社會?普通人此起彼伏的風險富人也逃不掉
很少有一部學術著作會像烏爾里希·貝克的《風險社會》那樣,出版、傳播直至譯介到中國的每一步,都像是踩著地雷,步步驚心。倒並不是這本書本身有多難翻譯,而是因為,其論述本身就與風險的大量湧現同步;這本書的每一次重要傳播,也幾乎都與全球性的風險相伴。也正是那一顆顆籠罩在頭頂、由現代化造就的定時炸彈,觸動了人們探究這一理論的熱情。
|
在《風險社會》中,這位德國社會學家勾勒了這樣一幅圖景:文明,而不是自然災害,正在把人類推上火山口。與普通人僅能從一個個事件中感受風險不同,貝克將一種新的社會結構,以及風險的生產邏輯完整地呈現在人們面前。
《風險社會》德文原版是1986年出版的。巧合的是,與書出版幾乎同時,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核事故爆發了。當年4月的切爾諾貝利事件,讓整個世界籠罩在惶惑與陰霾中。在這種集體情緒下步入大眾視野的《風險社會》,立刻引起轟動。6萬冊的銷量,對一部學術著作來說相當罕見。1992年,《風險社會》英譯本出版,貝克在知識界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風險社會」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研究領域,影響了安東尼·吉登斯、尼克拉斯·盧曼等眾多著名思想家。在輿論場中,貝克提出的「風險社會」也幾乎成了一種啟蒙,引導大眾關注那些一直被掩蓋的問題。
《風險社會》中譯本第一次在國內出版,是2004年。老版絕版多年後,譯林出版社今年終於推出了新譯本。在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肖瑛看來,與十多年前相比,直觀上,我們能看到風險正以更高的頻次,在更廣的範圍內出現,而且是此起彼伏,按住這一頭,那一頭又翹起來。比如,一戶人家如果沒有孩子,可能不會受疫苗事件影響;可這家人如果做投資,就不可避免地要捲入金融風險。從理論上說,隨著人們對世界的改造越來越深入,風險會逐步加劇。譯者之一張文傑則感到,如霧霾這樣的風險,已經從隱憂上升為全民關注的現實問題,「從這個角度看,貝克描述的圖景與普通中國人的感受更契合了」。
烏爾里希·貝克最熱的那些年
回看《風險社會》對中國人的影響,2001年的「9·11事件」是個重要節點。肖瑛記得,從那以後,「非傳統安全」開始在國際政治學界大行其道,這些討論,為「風險社會」的流行奠定了基礎。「如果說傳統安全問題就是國家之間的衝突,或者大規模的自然災害,『非傳統安全』則指的是超越國家邊界的、出人意料的恐怖襲擊。」肖瑛自己也是從那時開始研究「風險社會」理論的。
與遠在美國的「9·11」相比,2003年「SARS」更是讓每個中國人都切身感受到了威脅。「當時大家認為,SARS與歷史上的歐洲黑死病不同,不是純粹的自然災害,而是與人們的飲食、衛生習慣以及其他人為因素勾連在一塊。」加上口蹄疫、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風險社會」很快成了熱詞。當時,貝克與吉登斯、斯特科·拉什合作的《自反性現代化》已經出了中文版,國內一些學術刊物,如《馬克思主義與現實》,也接連推出了對《風險社會》的討論。
2007年,在一片風險社會研究熱中,貝克來到中國,並曾到訪上海社科院。回去以後,在接受德國媒體採訪時,他這樣表述對中國社會的看法:「首次中國之行令我感慨萬千,徹底改變了我對中國的認識,從日常瑣事,直至我的社會學說都有必要進行修正」「中國將資本和個人自由有機組合,或許會成為另一種現代組合模式。它比歐洲乃至世界對中國未來的推測都要穩定得多」。
相比於中文版剛推出的時候,肖瑛認為,「現在國內的研究已經不那麼熱了,相關研究越來越少」。但這並不意味著貝克的理論已被窮盡,或失去了對中國現實的觀照。「我們對風險的理解,還是比較淺層次的,只是想當然地使用這個概念,認為風險就是環境問題、經濟危機等等,而很少關注關於風險社會理論所討論的更深層次的問題,如科學理性的內在悖論、科學理性與社會理性的矛盾等。」肖瑛還指出,貝克所想像的科學理性和科學活動是獨立的,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它受政治、經濟、社會輿論等因素的深刻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對風險社會的研究,如果不考慮各種具體的在地化因素,那麼對它的理解就會越來越平淡。」
隱約有作為一名德國人的心理負擔
最新出版的這個譯本是以舊版為基礎,從英文版重譯而來,再根據德文原版做校對。在參與修訂的過程中,張文傑發現,英文版對原文改動較大,不僅省略了幾十頁內容,還在多處有漏譯和改動。針對這些差異,張文傑作了補譯、修正和說明,並重新翻譯了部分專業術語。所以,在行文和概念表述上,新譯本更接近於德文原版。
閱讀德文原版,讓張文傑直接地感受到貝克的語言風格。「語言風格平實、好讀。」他說,與同時代的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或更早的馬克斯·韋伯相比,貝克的表述方式都「更英美化,風格與吉登斯等人比較接近」。
貝克的書寫有時也頗為文學化,書中幾處浪漫的句子,甚至讓這位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感到有點為難,唯恐把握不準。「一般社科學者的寫作都力求精確,會努力避免出現這樣的句子。」可貝克顯然不想把這本書的面目弄得過於嚴肅,書中的許多句子都頗為活潑、感性。在前言中,他就大方寫道:「要是有人彷彿在字裡行間看到了閃耀的湖光,這不完全是錯覺。本書不少內容都是在施塔恩貝格湖畔的戶外山間寫成的,這裡時常天清氣爽,來自陽光、清風和水波的大量評註,一併被收在書中。」
寫作時,貝克常被湖光山色圍繞,但在書里,隨處可見他對環境污染的擔憂。「核能」一詞更是頻繁出現。二戰之後的西方社會大轉型,是貝克寫作的時代背景。在書中,他雖隻字未提納粹大屠殺,張文傑卻隱約感到,「他有作為一名德國人的心理負擔。他一直在試圖回答這樣的問題:如何才能避免人類走向自己也無法掌控的道路」。
專訪
第一財經:這本書出版後,「風險社會」一度成了一個時髦的詞。貝克所說的「風險」與自然災害或市場經濟中的「風險」內涵不盡相同,但他沒有對「風險」給出明確的定義。在你看來,貝克所說的風險究竟指什麼?
肖瑛:他說的「風險」是由人的理性決策和行動導致的。風險和危險不同。危險和人的行為沒有特別大的關聯,不管人在乎還是不在乎它,危險都在那兒。「風險」這個詞最早源於荷蘭的航海家。航海家不出海就不會遇到海難,但選擇出海,就可能遇到海難。因此,「風險」是人的理性行動的題中應有之義。
風險社會最根本的東西,是人類社會所面臨的自然已經完全被理性化的科學、制度所改造。我們現在雖然在說要「回歸自然」,但此「自然」並非真正的「自然」,而只是人造化的自然。人類行動的結果構成人所生活和生存的環境,因此,人類實際上就生活在風險社會之中。這是貝克所說的「晚期現代化」的特點。風險社會是現代化發展的高級階段,沒有人可以逃避風險社會。即使你是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看起來完全沒有對科技和理性發展起到作用或受其影響,但依然不得不承擔人類技術發展帶來的風險,就像環境污染。
第一財經:按照貝克的講述,富有的人抵禦風險的能力比窮人強,但現代化風險又有「迴旋鏢」效應,它最終會在總體層面上讓每個人都受到相同的損害,所謂「在現代化風險的屋檐下迫害者和犧牲者遲早都會合為一體」。他的這種論述如今是否還有很強的概括力?
肖瑛:我們現在就處在這種情境下。記得貝克說過一句話:「髒水不會在總裁家的水龍頭前停下腳步。」也就是說,風險社會面前人人平等。比如,疫苗事件,原先好像僅僅部分家庭是其受害者,但其實其波及面很廣,連劉強東的女兒也打了這種疫苗。還有如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好像沒有地球人能夠逃避其影響和危害。
當然,人們可以反駁說,具體地看,不同階層所面對的風險以及應對風險的辦法還是不一樣的。富人可以通過移民或其他方式來規避霧霾,可以通過打進口疫苗來避免假疫苗。但從根本上看,科學理性本身的內在矛盾決定了沒有一種科技產品對人而言的效果是完全積極的,有百利而無一害。而且,一種風險很可能帶來其他的風險,一個人可以逃避某種風險,但不一定能逃避由此帶來的其他風險。譬如三鹿奶粉事件後,據說中國奶粉的標準已經達到世界最高了,但是除了在經濟上無法支持的家庭,基本都會去吃進口奶粉。這就是由此造成的信任體系的破壞。社會信任關係被破壞後是很難修復的。這是一個很嚴重的風險,一個很少有人能倖免的風險。
第一財經:單身比例和離婚率越來越高,很多人對保持一段長久的關係似乎也不很熱衷了。直觀上,這些情況與貝克對核心家庭和兩性關係的論述十分接近。他在書中就提到,在風險社會中,穩定的核心家庭可能會搖搖欲墜,男女在人群中相遇,僅僅是互道好感,很快分手作別。這些生活狀態有什麼樣的大背景?
肖瑛:剛剛我們說的是生存性風險,在貝克的理論中,風險社會還有生活性風險這一維度,這就是個人迫不得已必須面對的個體化進程。西方社會在其現代化早期,民族國家會建立一套制度來保障每個個體的權利和自由,保證個體之間的平等關係。但風險社會是一個完全不確定的世界,早期現代化階段構建的保障體系無法再為個體提供保障,個體化因此而進入新的階段。
工業社會,男女雖然平等,但依舊講究核心家庭,講究男主外、女主內。但當個體化推進到極致時,女性也得到了和男性一樣的受教育和就業權利,經濟上獲得完全獨立。這樣帶來的結果是,勞動力市場更加擁擠,家庭成了一個協商性家庭。男女都要就業,孩子誰來帶?家務誰來做?就需要協商,因為已經不存在誰依賴誰了。而且,勞動力市場競爭加劇,催促人們不斷接受再教育,不斷流動,個體化反過來被不斷極致化。
這種流動性,讓國家很難建立保障制度。失業和就業的邊界日益模糊,上班不需要在特定的時間、空間內進行,失業率統計起來很麻煩。我們的很多畢業生不簽三方合同,開網店,或者在家玩電游,也能賺錢,很難在制度上確定他們是失業還是就業。個人也不知道什麼制度有利於他,只能不斷再學習,但所有制度都是供個體選擇的,而不具有保障的作用,就如現在的考證熱,多一個證書對於個體而言就多一個就業機會,但這些證書本身也並不保障能夠就業。另一方面,個體是可以建構制度的,但制度建設不是單個個體所能完成,而需要同他人協商、合作,雖然這種合作很可能是短期的,因事而起因事而終的。所以貝克說,風險社會中,人要有一種利他的能力,但這種利他背後還是功利主義。
與此相關聯的就是「亞政治」的興起。個體聯合起來,就某一個風險現象,發起社會運動,通過社會理性來監控和防止科學理性的肆無忌憚。這一點,最典型的是崔永元等社會人士發動的反轉基因運動。很多人認為,他們不是科學家,不懂轉基因,就不能質疑它。但按照貝克的「亞政治」理論,崔永元並不是在反科學,而是通過互聯網,發起一場新社會運動,要求清楚標註哪些產品是轉基因產品,哪些產品是非轉基因產品,把食品選擇的權利交給消費者。這就是用社會理性來應對科學理性的一種表現,希望以此來對風險社會的進程進行一些控制。
第一財經:《風險社會》出版多年之後,在你看來,他書中的哪些內容得到了尤為強烈的現實印證?
肖瑛:風險社會所呈現的是晚期現代化階段全球社會的整體狀況,但我們每個人都很難抽象地理解風險社會,而是去感受一個一個具體的風險現象。不同制度、文化和經濟情況下,具體風險現象以及它們的生產和再生產邏輯不一樣,人們對風險現象的選擇和理解也不一樣。比如,身處貧困中的人對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的感知就與大城市的白領不同。貝克用「亞政治」來呼喚人們在風險社會中的積極行動,也只能是針對具體的風險現象,而難以抽象地反對風險社會。
直觀地看,具體的風險現象在我們的生活中起起落落,此起彼伏。但是,在學術上,對具體風險的理解,必須與風險社會這一整體階段勾連在一起,是整體的風險社會生產機制在特定條件下的具體化;而且,從社會整體結構來看,具體風險的規避和生產是同一個過程,按住了這一頭,那一頭可能就會翹起來;反過來,具體的風險現象的不斷湧現,實際上也推進了風險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
|
《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
[德]烏爾里希·貝克 著
譯林出版社2018年2月版


TAG:第一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