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雅評《董小宛入清宮與順治出家考》︱清代疑案與疑案考據
原標題:王敬雅評《董小宛入清宮與順治出家考》︱清代疑案與疑案考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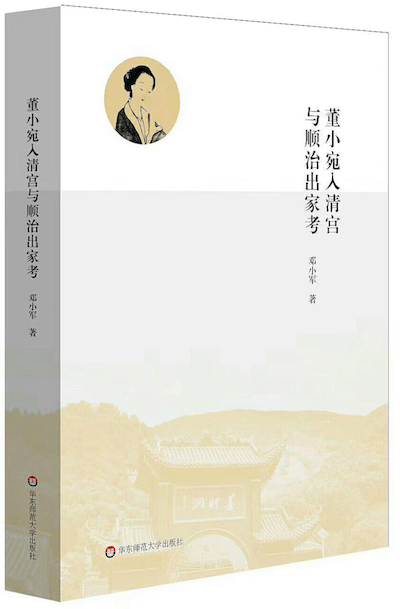
《董小宛入清宮與順治出家考》,鄧小軍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488頁,98.00元
民間廣為流傳的「太后下嫁」、「順治出家」和「雍正即位」三大疑案,向來是為人樂道的傳奇故事,自清初至今一直是好史者的飯後談資。孟心史先生作《太后下嫁考實》《世祖出家事考實》《世宗入承大統考實》三篇,將傳說與史實互相印證,以史家之嚴謹慎密考證了「順治出家」這一疑案。此外,陳寅恪、陳垣、鄧之誠等幾位學者,也對「董小宛入宮」提出過自己的見解。
明清鼎革之際的歷史頗有特點,一則相對於前代,清代所留文獻豐富,尤以詩文較多;二則時局動蕩,人物命運坎坷,有較強的故事性。這就造成此段歷史研究的兩個特點,一是官書檔案保存不全,需以私人記錄補齊,所以史料甄別極須謹慎;二是歷史細節較多,難以形成定論。
在此情況下,重新考證清初歷史,就需要很強的耐心和文獻收集、考證的能力,首師大鄧小軍教授的新作《董小宛入清宮與順治出家考》重新梳理明末清初這一段史實,並得出了較為新穎的結論。
清史文獻價值的界定和文獻的選用
鄧書非常重視史料的「原始性」,但是史學研究中,並非越「原始」的史料越有價值。作者對史料選取的宗旨是,「董小宛入清宮與順治出家史事的相關程度不同的原始文獻,除官修史書、宗譜、年譜、方誌、禪宗文獻、朝鮮文獻、石刻文獻等之外,還包括順康間人的詩文,甚至戲劇,其中包括順治、康熙御制詩文」。但是這些史料並非價值等同,也不一定都符合歷史事實。
書中在論證「董小宛入宮」一事時,反覆提及李渲《燕途紀行》和冬至正使尹絳的《燕中聞見》,前者是清主親兵哨官朝鮮人金汝輝述順治董皇貴妃,後者則是朝鮮使者的見聞。此類記載中對董小宛進宮言之鑿鑿,但並未說明傳言出處。對清代皇帝,朝鮮使者有很多傳言,如「孝庄文皇后與孝康章皇后婆媳不睦」、「康熙皇帝好色」等,均源自朝中傳言,或是街頭巷議。孔子曾經說過:「道聽途說,德之棄也。」所以歷史研究在選取民間傳說的時候需要非常慎重,如果採信傳說,則定要對傳說的來源與流變加以分析。
書中言及董鄂妃即董小宛一事,前列實錄,後書《燕途紀行》,再後為《燕中見聞》,這兩則史料中談及董鄂妃非鄂碩之女亦是揣測,沒有明確證據。而作者論斷:「根據上文考察,可知順治董皇妃即董小宛,清廷官方文獻稱董鄂妃乃滿洲族內大臣鄂碩之女,是掩人耳目之謊言。」以使臣見聞證官書之偽,為治史一大奇事。除此之外,書中還以偈語證史。眾所周知,順治帝與玉林通琇、茆溪行森等僧人交往過密,在討論順治出家這一問題時,這些僧人的言論經常被引證。但本文以茆溪行森之偈語逐條證明董妃行狀,存在過度解讀的情況。
本書有規範的論證格式,每句皆有「古典」、「今典」,可見其旁徵博引。然而歷史論證與文學不同,對某觀點的論證,求要不求備。本書的一個特點便是,凡是與詩句相關,無論繁簡皆列述其後,於史實則大可不必。書中翰林院檢討李天馥的詩文《古宮詞一百二十首集唐》被認為是「董小宛入宮」的重要證據,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曾提及此事,稱此詩「蓋為董鄂妃作」,被作者加以發揮。翰林院檢討有「纂修史書、重纂實錄、聖訓、玉牒」之責,讓人很容易聯想到白樂天的《長恨歌》。李天馥此詩是否紀實,尚不好定論,因其人時為文壇翹楚,文採風流,著有《容齋千首詩》《容齋詩餘》。王世禎稱「二公(謂李天馥、陳廷敬)嗜好略相似,每下直日,必相聚,聚必相與研六藝之旨、窮四始五際之變,至參橫日落,然後散去」。而又好作風流之詞,相傳「居京師時,雅好冶遊,有伶人新婚,戲為《賀新郎》詞一闋」 (李定夷《軼聞大觀·第二編》卷二)。這樣一位才子,寫宮詞並不是特例,在清初屢有所見,稱其詩必定暗示順治後宮,似乎不妥。

《古宮詞》
河南省民權縣白雲寺石碑,也是書中非常重視的一處文獻,其實作者所採信的順治出家白雲寺一事,亦非空穴來風,乃是當地的一個傳說。康熙為了尋找隱名出家的父親順治南遊白雲寺,遇到一位自稱「八乂」的燒鍋僧人。康熙回京悟出「八乂」合成一個「父」字,恍然大悟,二下白雲寺,但老僧已不知去向。康熙只得御書「當、堂、常、賞」四個大字,意含將田、土、巾(布)、貝(錢)賞賜僧眾。關於順治出家的傳說在後世版本很多,本書顯然採信了河南民間這個故事,但沒有提及故事的來源,更沒有考證。而這種傳說如果作為史料,第一步就是要考據其真偽源流。
歷史問題證明的邏輯性
「孤證不立」是歷史研究中的又一基本原則,因此,研究者需要就某一問題充分收集材料,以達到從多角度佐證歷史的目的。「孤證」並不代表數量上的單一,同樣也指角度上的單一。因此在證明某些問題時,邏輯上要求有遞進關係,而非內部自洽。
文人交遊是明清之際歷史研究的一個重點,其中社科院趙園先生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頗為可讀。由上述研究我們可知,清初文人有很多並不封閉的交往圈,他們的興趣和風氣極為相似。冒辟疆、陳維崧、吳偉業、徐泰時、周士張、丘石常等人本身就組成了一個文化交際圈。清初南方士大夫之間,本來就風氣相通,聲音相和,這些人又同在一個社交圈內,處於社交網路的相通層級,他們的詩文在史實上不能形成互證。冒辟疆《影梅庵憶語》洋洋四千言,回憶了他和董小宛纏綿悱惻的愛情生活,才子佳人本身就是文壇中長盛不衰的話題。冒襄本又是風流之人,當時與江南名妓交往甚密,是當時文人津津樂道的掌故之一。不僅董妾如此,後來冒續娶的吳妾、張氏等人。他的好友金壇張明弼在《冒姬董小宛傳》中不無打趣地說,冒氏「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為貴人婦,願為夫子妾者無數」。這些文人,本身就是一個互相講故事的圈子,這個圈子之中故事可能共同表明某種現象,然而互相證實,於史則不可。
此外,歷史的發生有前後邏輯,以後證前時,尤為慎重。如作者認為,詩文中「漫說蓮花國,蓮花國在西」中蓮花國指滿洲,所徵引的史料是乾隆年間成書的《滿洲源流考》,因為書中有云:「曼珠,華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這種證實顯然是缺乏歷史邏輯的。眾所周知,《滿洲源流考》是乾隆皇帝為滿洲發端尋求合法性的作品,中將滿洲源流回溯至文殊師利,是乾隆皇帝接受藏傳佛教思想後的一種自我合法化,並不能證明在明末清初,文人常識中將「滿洲」與「曼珠」是直接關聯的。這種將政權源流佛教化在歷史上很常見,特別是蒙藏地區,滿洲人成因了這一習俗。將清初文人詩作中的「蓮花國」直接對應為滿洲政權,以後證前,以多證一,實在是難以令人信服。
歷史常識與趨勢
1927年,王力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做研究生論文《中國古文法》,指導教師是梁啟超、趙元任兩先生。趙元任先生在眉批中有這樣兩句話:「未熟通某文,斷不可定其無某文法。言有易,言無難!」此兩句尤其適用於本書。大膽推斷之後,接下來務須加以詳細論證。但本文似乎只做到了前半部分。
當然,歷史考據的存在意義並不止於考據學本身,而是對歷史場景的還原。如書中在考證董小宛有可能被劫持入宮時,對清初滿洲人劫掠漢人婦女的情況做了一些梳理,這種考證是有價值的。對董小宛入宮的確實性,作者則說:「多爾袞派人擄走江南之有夫之婦董小宛,亦是完全可能之事。」這個說法似乎太過武斷,而本書在這種關鍵性的問題上,幾乎都是這樣在萬分之一的可能性間,下了確實性論斷。
文中言及冒辟疆上京討妾,冒襄以堅不仕清聞名當世,康熙年間,清廷開「博學鴻儒科」,下詔征「山林隱逸」。冒襄也屬應徵之列,但他視之如敝履,堅辭不赴,且家中妻妾成群,焉有主動赴京之理。且其赴京在順治末年,南方尚未平定,民變亦有發生,一書生安可平安上路?其行程時間參考康熙二十三年南巡,絕無可比性。
朝鮮《顯宗實錄》的記載,康熙五年(1666)九月,朝鮮國王顯宗詢問是朝鮮入清使臣許積曰:「順治好漢語,慕華制雲,今則如何?」許積回答道:「聞其太后甚厭漢語,或有兒輩習漢俗者,則以為漢俗盛則胡運衰,輒加禁抑雲矣。」雖然此為朝鮮使臣道聽途說之語,但是參考孝庄文皇后所首肯的順治遺詔,起首便是:「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謨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漸習漢俗,於淳樸舊制日有更張,以致國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可見孝庄皇后不僅不慕漢語,更厭惡漢俗。換句話說,孝庄皇后漢語能不能表達清楚都成問題,安可與冒襄做此交易。
如果說董小宛入宮,作為一個小人物的歷史,還存在著某些可能性的話,那麼順治出家一事,必須要嵌入清初的歷史政局中加以考察。文學作品與影視作品中常有的想像,就是用作者個人的社會角色,去揣度皇帝的社會角色,於是認為皇帝和普通人一樣,只將感情局限於個人層面。
再於「順治出家」一節,作者認為,康熙皇帝之所以多次西巡,著意大規模興建五台佛寺,乃是為其父造一安身之所。然而最基本的常識是,順治即使真的出家,照記載來看,也是皈依漢傳佛教,而康熙著力將五台山打造成為內地藏傳佛教中心,並有章嘉、哲布尊丹巴兩位大活佛的駐錫地。此舉於順治出家並無關係,即使有影響,也是消極的。此外,書中稱,王熙順治駕崩的見證人,並未言及順治死狀,乃因順治假死。須知清代歷朝皇帝死前,皆有近臣在側。
而文中第十一章還言及,翰林院庶吉士親書寺廟地租碑,知州親命勒石,是對白雲寺的特別重視,並將此作為順治出家白雲寺的一個佐證;康熙厚賜玉明和尚、厚賜白雲寺,意在照料順治。須知康熙朝敕建寺廟無數,御賜匾額更不勝記。一則其一生六次南巡、六次西巡、常年巡幸京畿、所駐蹕之地若為寺廟,則有題字。之後,作者認為順治皇帝死後,白雲寺為其修有陀羅尼經幢。民權白雲寺經幢並不只此一通,另有「佛公靈塔經幢塔」,上書「佛洞宗三十一式佛公大和尚」,乃是佛定圓寂後,河南布政使牟欽元親自為他寫了塔銘。顯然經幢並非孤立,地位也不是獨尊。作者所見「□王宔」之匾,將其識讀為「先王宔」,解釋為先帝的神主。但是「先」字為作者自己識別所加,不一定為原有脫字。而「宔」字為宗廟藏神主的石函,《康熙字典》的解釋為「以石為藏主之櫝也。一曰神主。左傳:許公為反祏主。本作宔。通作主」。某王似一宗教稱謂,清代皇帝稱自己的父親為「先皇」、「皇考」,絕無用「王」字之例,而王另有別稱。

「(先)王宔∣當堂常賞」匾額及拓片,圖片來自鄧小軍著《董小宛入清宮與順治出家考》
在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時,需要有較為廣闊的觀察視角。此時,北方外蒙諸部尚未平定,青藏地區時時攪擾,內部民變未熄,南方從對戰南明到平定三藩,全國一直處在一個動蕩的局勢中。即便是做微觀歷史事件的研究,尚須從此處出發,更何況帝王政治。
也談清史中的「詩文證史」
「以詩證史」是現代史家頗為推崇的一種治史方法,它可以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狹義的「以詩證史」就是用詩為史料來證史說史;廣義的「以詩證史」可泛指以文學作品用作史料來研究歷史,舉凡中國古代的詩詞、文論、小說、寓言,乃至政論文章,都可包括在內。
「詩文證史」首推當屬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作者鄧小軍先生也是如此,然鄧先生在詩文引用時,恰沒有注意到陳寅恪非常注重的一點,就是用史實對詩文的考證。如《胡旋女》一節,陳先生引樂天詩:「梨花園中冊作妃,金雞障下養為兒」,之後說道:「唐長安有二梨園,一在光化門北,一在蓬萊宮側。其光化門外者,遠在宮城以外。其蓬萊宮側者,乃教坊之所在。准以地望與情事,似俱無作為。冊妃處所之可能。樂天之言未知所據,又太真外傳上雲……其事在天寶四載八月冊楊氏為貴妃事以後。准以時間,亦殊不合。故於此冊妃之處所,惟有闕疑,以俟更考。」簡言之,作者的歷史常識與詩文內容間,應該是一個正向輸入的過程,而不是以詩文定義史實。不完全統計,《元白詩箋證稿》中,所引唐代各類史籍凡逾百種,而如論清代歷史,史書只可見《清實錄》,豈可成文?
而詩文、小說最可用之處,在其「不經意間」,而非其刻意記錄的故事。如《時女妝》一段。陳先生云:「樂天則取胡妝為此篇以詠之。蓋元和之時世妝,實有胡妝之因素也。凡所謂摩登之妝束,多受外族之影響。此乃古今之通例,而不須詳證者。又豈獨元和一代為然哉?」陳先生又云:「豈此種時世妝逐次興起於貞元末年之長安,而繁盛都會如河中等處,爭時勢之婦女立即摹之。其後遂風行於四方較遠之地域。迄於元和之末年,尚未改易耶?今無他善本可資校訂,姑記此疑俟以更考。」以詩文考時風,尚有存疑之處,以故事入正史,豈可言之鑿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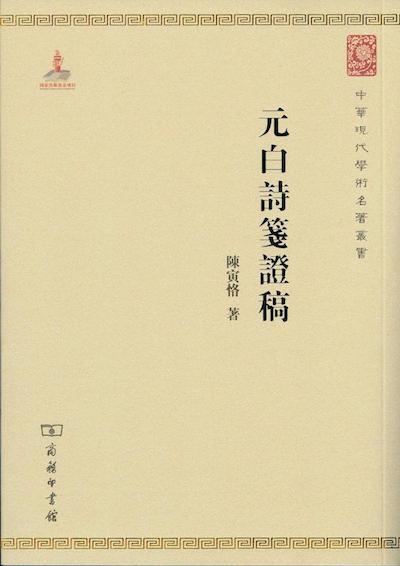
《元白詩箋證稿》,陳寅恪著,商務印書館2015年5月出版
詩文中證實時風世俗易,證確鑿人事難,在史學界是公論。此法似乎最是高妙艱深,非常容易滑向主觀臆造的一端。在文學作品中過於求深、刻意求實,結果反而失真失實。呂思勉先生曾說:「諸子中之記事,十之七八為寓言;即或實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多不可據;彼其意,固亦當作寓言用也。據此以考事實,苟非十分謹慎,必將治絲益棼。今人考諸子年代事迹者,多即以諸子所記之事為據。既據此假定諸子年代事迹,乃更持以判別諸子之書之信否焉,其可信乎?」
呂先生雖言先秦,於清代亦然,而更有甚。清代史書品類繁多,為歷代所不及。先秦史研究中,很多時候除了諸子文獻,別無史料可引,清史研究中此類狀況絕少。清代官書以實錄為紀年之綱要,各類檔案系年而記,兼以第一人筆記輔之,詩文則又次之。在史料佔有不完全的情況下,很難判斷歷史細節的真偽。
此書材料豐富於前代,而格局未及,與孟森先生作品相比,作者似不具備治史之常識。其實,疑案的考實,並不是為了追求疑案本身的真偽,而是對作者和讀者的思維練習,有些類似推理小說,而考據的樂趣即在其中。本書開篇曾言,作者因為佔有了新的史料,而務須重談疑案,其實其所佔有之史料,言新則新,於史實本身並無決定性作用。考據文章大可不必如此,舊史料作出新意境,舊問題考出新邏輯,便是上佳之作。本文亦沒有就史實發微,僅就考證過程置喙一二,然而開卷有益,書中引用了大量詩詞,為研究清史書籍所少有,不管成功與否,算是正方向的嘗試。


※杜嘉班納事件:當東方不再接受西方的審美「馴化」
※徐美潔︱方孝孺與蛇王廟
TAG:澎湃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