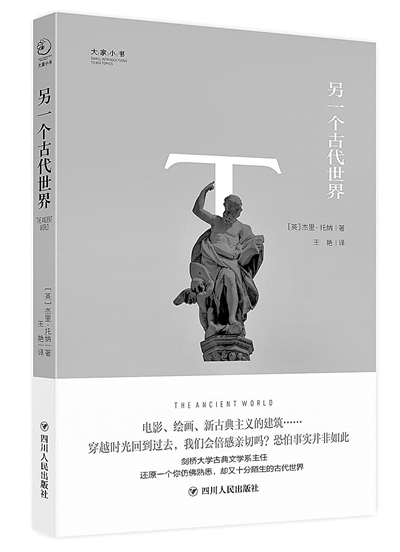從大汗的一碗羊湯看全球化
原標題:從大汗的一碗羊湯看全球化
|
|
《另一個古代世界》 [英]傑里·托納 著/王艷 譯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10 |
|
范一
你也許認為古代世界早已煙消雲散,但它就在那裡。看不見是因為你不想,只要你想,就立刻會意識到它無處不在。
深度閱評
天曆三年,在宮中供職多年的飲膳太醫忽思慧,將自己為蒙元皇室調理膳食的經驗,編寫成《飲膳正要》一書,進獻給當時的元帝圖帖睦爾。
忽思慧在上書給元帝時一再使用「諸珍異饌」 「奇珍異饌」等言語,特地強調那些被用在膳食中來調養身體的稀貴食材。
正如他所指出的,鐵木真及其後人通過不斷征戰將其疆域擴展到人類歷史上空前廣大的地步,幾乎大半個歐亞大陸被納入同一個帝國的統治之下,「伏睹國朝,奄有四海,遐邇罔不賓貢,珍味奇品,咸萃內府」,昔日被視為來自異國殊方的奇珍,被納入帝國境內的共同市場。在忽思慧向大汗進獻的各色營養食譜之中,出現了眾多有著異域風情名稱的食材,其中就有據稱可以「補益溫中順氣」的馬思答吉湯。
馬思答吉湯的做法是:羊肉一腳子,卸成事件。草果五斤、官桂二錢、回回豆子半升,搗碎去皮。右件一同熬成湯,濾凈,下熟回回二合,香粳米一升,馬思答吉一錢,鹽少許,調和勻,下事件肉,芫荽葉。
這道湯得名於在全部食材中僅佔一錢分量的「馬思達吉」,單看其名字很難知曉其為何物,但是湯既然以此為名,可見其分量雖然輕,卻很名貴。明人謝肇淛在其《五雜俎》中只有簡單的十幾個字,介紹它出自西域的一種香料,「似椒而香酷烈,以當椒用」;而同時代的李時珍已經不知道馬思答吉是何物了,只是《本草綱目》菜部的蒔蘿條下順便附錄馬思答吉,「元時飲膳用之,雲極香料也,不知何狀,故附之。」
明人之於馬思答吉變得生疏的情形,一則是因為馬思答吉可能是貴重香料,不易得見,一則是在世界帝國崩潰後,異國殊方的奇珍要經由更加曲折的跨國貿易才能抵達,更加不易得到。這個詞幾乎不再現身,只是在後世的本草類文獻中,跟熏陸香、馬尾香等名目一起被當作是乳香的別名。而把熏陸香、乳香視為一物的觀點也沿襲於《本草綱目》,李時珍聲稱「乳乃熏陸中似乳頭之一品爾」,言之鑿鑿地把乳香當作熏陸香的一個品種。
事實上,早在蒙古征服之前的宋代,乳香早已被長期進口並廣泛使用,僅僅是宋初的建隆四年,南唐的泉州清源軍節度使陳洪進就曾派使者向趙匡胤進貢大量乳香,「乳香、茶葯皆萬計」,宋人對其必定相當熟悉。身為宋宗室的趙汝適,算起來是趙匡胤的八世侄孫,卻「不務正業」地愛好地理,在其著作《諸蕃志》中記載「乳香,一名薫陸香」,似乎這就是李時珍所持觀點的淵藪。
然而,比趙汝適早一百多年的洪芻看法不一樣。洪芻是宋代著名的西江派詩人黃庭堅的外甥,詳細記載當時能夠從生活和文獻中見到的各種香料,並在著作《香譜》中明確區分熏陸香、乳香。他指出乳香是海外波斯國的松樹脂,而分泌熏陸香的樹則出自海南,也被叫作「馬尾」。
沿著歷史長河的暗流上溯,早在馬思答吉出現在蒙元御醫筆下的一千年前,一本中國的植物學著作指出,熏陸香出自大秦。
當時中國人稱呼遠在極西的羅馬為大秦國,這本由「竹林七賢」之一嵇康的侄孫嵇含所著的《南方草木狀》記載,大秦國的海邊有枝葉如同古松的大樹,生長在沙地,盛夏的時候,樹上流出樹脂,流溢在沙上,就可以採集了。
嵇含生活在西晉,他出生的時候距離後漢時期甘英出使大秦國已經至少一百五十年了,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因為聽聞海中的風險而止步,而在他的眼前泛著的波瀾,可能正是在荷馬筆下有著「深酒紅色的海面」的愛琴海。
希臘的希俄斯島據說是荷馬的故鄉。如今,每年七月,希俄斯的島民就開始清理乳香黃連樹附近的地面,撒上石灰粉,然後在樹榦與樹枝上切口,等樹脂緩緩流到地面,凝結成塊,再將其採集並清洗,花上整個冬天提煉成香料,這個過程跟一千八百年前嵇含的記載如出一轍,而嵇含又摘自三國時期吳國萬震所著的《南洲異物志》——萬震補充說,「狀如桃膠,夷人採取,賣與商賈,無賈則自食之。」
這種希臘「夷人」採擷的樹膠名為Mastic,在阿拉伯語中被轉寫為Mastaki,音譯成華語則正是忽思慧寫入羊湯食譜、李時珍「不知何狀」的馬思答吉,迄今尚被希臘人用來製作香口膠或香精。至此,一段隱秘的身世水落石出,古典時代的熏陸香、蒙元時期的馬思答吉是原產希臘的一種香料,而絕非來自西亞及北非阿拉伯世界的乳香,而今天的醫書藥典仍然將兩者混為一談。
唐宋時期的海上貿易發達,獻給趙匡胤的乳香來自福建的泉州,唐代的鑒真記敘廣州「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計其數……香料、珍寶積載如山」,李翱在其文章中提到「異香、文犀,皆浮海舶以來」。
在波斯滅亡之後,大食商人成了海商中的主角。從巴格達經底格里斯河進入波斯灣、經過印度洋,過新加坡進入南海、北上廣州的航線,是在帕米爾的怛邏斯戰場上被大食人俘虜的杜歡,從巴格達脫身歸國的路線;也是楊良瑤神道碑的主人在貞元年間奉旨出使大食,從廣州出發後極可能採用的路線——楊良瑤神道碑記載了「黑夜則神燈表路」的波斯灣燈塔,其出使往返「星霜再周」,全程僅用兩年時間。很顯然,這是一條足以讓大宗商貨流通的安全、可靠的路線。
隨著大食商人成為連接東亞、歐洲和北非的海洋貿易主導者,其重要特產阿拉伯乳香也成為輸往東方的大宗商貨,熏陸香很可能在這個過程中漸漸模糊了自己的面貌。
在「奄有四海,遐邇罔不賓貢」的蒙元時期,以絲綢之路著稱的陸路商道變得順暢、安全並擁有來自同一個家族的統治者,曾經是遙遠異域的大食國也一度被納入境域之內,於是熏陸香原本的夷名遂獲得直接傳入東方的機會,成為可汗餐桌上羊湯里的「馬思答吉」。
今天,可汗與馬思答吉湯早已消散為歷史的灰燼,但是已然置身全球化世界的人們依然受惠於兩千年前就已經形成的世界交流網路。儘管大多數歷史學家認定全球化開始於十六世紀,但是顯而易見,對於從馬思答吉貿易中受惠的人們——無論是收割樹膠的島民,還是水手、商人、搭乘船隻的僧侶、收取稅務的官員,以及最終享受這種香料的貴族、君主、寺觀的法主、把它當作藥物的病人——都早已深深地捲入前現代的全球化進程之中了。
一如美國的歷史學家麥克尼爾父子指出的那樣,兩千年前,人類社會已經形成了涵蓋歐亞大陸的舊世界網路體系,並不如杉山正明或岡田英弘所說的那樣,要等到忽必烈之時才有世界史的誕生。
事實上,全球化比人們想像的要早得多,對形成今日世界的影響也比當代人自以為是的看法要重要得多,「你也許認為古代世界早已煙消雲散,日常生活中你也許注意不到它。」正如英國的古典學者傑里·托納博士在其作品《另一個古代世界》中所說,「但它就在那裡。看不見是因為你不想,只要你想,就立刻會意識到它無處不在。」
托納博士的這本書從大眾化社會生活去展示古代世界的另外一個樣子,特別是從羅馬龐貝城遺址中不被人留意的細節去考察羅馬帝國,並將古典時代的羅馬與中國稍作比較,甚至順便提及今天生活在中國驪靬的村民很可能跟在塞琉古戰敗的羅馬軍團有關的傳言,當然他也指出這種可能性無法證實。作為一本富有趣味的讀物,講八卦故事並非托納博士的目的,有些資訊可能已經不算新鮮了——但是這並非重點,重點是人們該用什麼樣的眼光去窺探古代世界。
「我們也許會認為,我們已經從久遠的古代邁向現代世界,所以不再受其影響,對其心存偏見,但是這麼多世紀以來,我們總是受到古代思想和被它們引起的共鳴強烈吸引,忍不住回望。即使我們想完全拒絕古代世界,最終也只會發現我們原來只是給自己重新定位而已。」托納博士在《另一個古代世界》中如是說。他並不試圖告訴人們古代世界有什麼,而是啟發人們去重新認識古代世界,就好比一碗羊湯中的全球化。
人們大可以將全球化做出不同層面的分野,諸如商業的全球化、工業的全球化、金融與服務的全球化,以及剛剛降臨不久的信息全球化。與其將蒙古的擴張視為全球化的開始,倒不如將其視為早期全球化時代的結束,即用武力終結了純粹基於貿易利潤的全球化網路體系的編織過程。當然,僅僅用武力打通歐亞非大陸而強制形成的統一市場,必然很快在各種利益訴求面前土崩瓦解。現代世界所承接的,仍然是早期全球化的成果並在廣度與深度上加以豐富。
現代世界再無大汗的羊湯的蹤影,但我們仍然能夠在模特、香水商和時尚的擁躉的身邊感受它的來去之路,從對歷史的繼承中找到自己在當下世界的位置。這就是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說的,「我們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寫歷史,因為每個時代都會產生新問題,探求新答案。」


※容祖兒:「娛樂圈勞模」劉德華是榜樣
※緊要關頭,才知道自己無關緊要
TAG:北京青年報 |